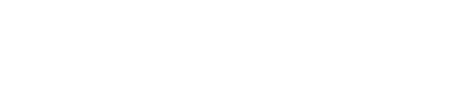韩小蕙(中文系1978级本科生,作家 光明日报《文萃》主编)
我们南开有着极棒、极出色的一个教师群体。我从他们那里终生受益,至今心心念念,有一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殷殷亲情。
1978年秋天,我在做了漫长的8年青工之后,终于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实现了似乎已经永远离我而去的大学梦想。
跨进南开校园的第一周,整个一颗心始终都是坐在炉子上的沸水壶,“咕嘟嘟”地沸腾着:看到花叶葳蕤的南开校园,兴奋;看到绿波荡漾的南开湖水,兴奋;看到高耸入云的教学大楼,兴奋;看到周恩来总理纪念碑以及他的题词“我是爱南开的”,兴奋;看到洁净明亮壮阔的图书馆里有那么多藏书,兴奋;看到从全国各地考来的各位同学精英,兴奋……
然而后来最让我兴奋的,还是我们南开有着极棒、极出色的一个教师群体。我从他们那里终生受益,至今心心念念,有一种“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殷殷亲情。
初上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时,大家都没重视。况且,宋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下马威,板着硬脸,很严厉地斥责我们班上一位逃课的男生:
“进大学,是叫你们读书来了,不是让你写小说来了!不好好上课,躲在宿舍里写小说,歪风邪气!”
“不想上课的,退学!把位置让出来,有的是人想进来呢……”
当时大家都倒抽一口冷气:这老师可真够厉害的!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了抵触情绪,因为谁上大学不是冲着作家梦来的?何况当时新时期文学又是初露端倪,写小说之风特别兴盛,像我,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写了好几年,发表过两篇了,怎么舍得就此罢笔?再说,我从小学起就讨厌语法,什么“主、谓、宾,定、状、补”,多么枯燥,不懂它们怎么了,那么多作家不照样写小说?全照它的模子套,还写不出来了呢!
可是本能又告诉我,宋老师说的可能是对的。搞创作,上完大学还可以继续,眼下这课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自己的基础本来就差,再不全心全力上课,一辈子都会跟不上趟。我当时心里矛盾得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谁想宋老师不仅毫不客气地训我们,还苦口婆心地教,还讲究方式方法,更有高超的教学水平。没几天,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把我们全班大大小小,一股脑儿全装进他的“牢笼”里,我们全成了他的“俘虏”。他讲课的时候,也不声高,也不卖弄,也不急躁,也不斥责,也不喋喋不休,也不拳打脚踢。只是不急不慢不温不火循循善诱,出神入化地,就把我们这群不怎么愿意听话的“野羊”,领进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宏伟殿堂。这时候再看“主谓宾,定状补”、“偏正结构”、“把字句”,不但不再使我们绕着脖子也弄不明白,因而厌烦之、痛恨之,而是成了吸引我们钻进去探险的“仙人洞”,有一阵子,同学们特爱在一起分析汉语“玩”,有的同学还“玩”上了瘾,后来,居然就将“语言学”选择为终生职业。
于今想来,30年都过去了,我还是没搞明白,当初宋老师到底给我们施了些什么“魔法”,怎么就让我们乖乖地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完成了这门功课?可以说现代汉语语法是我在南开4年里学得最好的一门课,实实在在学到了东西,吃进肚子里面去了。当我大学毕业进光明日报社以后,正赶上报社不少同志补上夜大学,他们拿来了不少语法分析难题,请我们这些来自各个大学的“七七级”和“七八级”做。有人吟哦半天做苦思冥想状,我呢,拿起来一挥而就,手到擒来迎刃而解,大大为我南开露了一次脸。我心里真怀念宋老师,后来才听说,他教我们时,正是他的家境极为艰苦的时期,经济上比谁都拮据,搞得他精神负担极重,可他还是那么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呕心沥血,卖命不要命地教诲我们,表现出高尚的教师人格。
中文系还有号称“四大才子”的四位古典文学老师,风格很不同,有内向深沉型的,也有翩翩才子型的。宁宗一先生是典型的文人才子,平日里但见他把腰杆一挺,头发一甩,就口若悬河地侃侃而谈,大概是我行我素惯了,有时才气外露到咄咄逼人的程度,也一点儿不惧怕外界舆论,看来他是绝不把“夹着尾巴做人”奉为处世哲学的经典。郝世峰先生则是深不可测的一口井,高高的身躯只给人一个“高”的感觉,不傲,不急,不躁,很谦和很沉稳很有书卷之气,后来他果然就主政中文系,搞得很有中兴的气象。鲁德才先生倒是常能见到,听说他的学问很好,心里面存了尊敬。还有一位大才子罗宗强先生,他原来是中文系的人,可我们上学时被调到《南开学报》去了,“七七级”有的同学的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非常出色,成为范文,罗先生也就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可惜这四大才子一个也没有教过我们,只能远远地仰望——那时我还是一个非常羞涩的小女生,没事的话,绝不敢主动去跟老师们瞎搭茬儿。
教我们古典文学的先生也姓郝,郝志达老师,他也是一位严师,对我们要求得一丝不苟,也没任何客气好讲。记得讲到《诗经?东山》时,一共四段,他指定我们背诵第一段和第三段,说是下节课要检查。到了下节课,说到做到,果然就检查,而且他知道我们女生老实,偏偏叫起两位男生,一人一段。这两位男生可真为我们班争气,不仅悉数背上,还琅琅上口,喜得郝先生连连点头,从此对我们班免却背书检查。
我很感激郝先生的严,《东山》全篇当时都背下了,记得就特别的牢。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福建省东山县去写报告文学,采访对象是当年被国民党抓丁到台湾去的老兵遗属,我心里不停地涌起《东山》诗句。回来动笔写作时,我采来《东山》诗古意,并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作为全篇的主调,回环往复,增加了感人的力量。由此可见,当年老师们要求我们好好读书的话还是对的,心中没有诗书垫底,文章也根本写不好。
后来学唐宋时期文学,教我们的是一位女老师,名叫张虹,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是老师,其实她也就比我大几岁,实际年龄还不如我们班好几位“老生”大——这也是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奇观,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的大学11年没有招考,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时,全国有10届初高中学生一起投入高考,一起入学。所以,我们“七七级”和“七八级”,从16岁到32岁的学生都有,也算创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张虹老师虽然年纪小,可是她早几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入学,由于成绩好表现优秀,遂被留校当了老师。在当时的南开中文系,她是年龄最小、资历最浅的,可是她非常要强,日夜苦读,殚精竭虑想要把我们教好。看她往讲台上一站,摆开架势,专业术语一串又一串熟练地甩过来,我们大家心里还真肃然起敬。不过她到底又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年轻女孩子,平时愿意和我们女生走近,有一次聊天,她听说我写了一篇小说,非要看看。我心说你是搞古典的,怎么也看当代小说呀?没想到她看完以后,居然按照古典文学的分析方法,把人物、结构、思想性等等分析得头头是道,让我心服口服,对我后来的修改给了很大的帮助。而且最重要的是,从此我方知道,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若是在高位,做什么学问都是相通的,这大概就是“融会贯通”的境界吧?可惜的是,偏偏考张虹老师的课时,我因发烧没考好,只得了80分,这是我在整个大学期间最低的分数,到现在都心存歉疚,觉得对不起张虹老师。
从1982年毕业离开南开到现在,已经26个年头了,时光真是一道闪电,那么快地就过去了!但我的南开,我的老师们,一直始终还镌刻在我的心头,永远不敢忘其恩情。
宋玉柱老师、郝志达老师,还有崔宝衡老师、郎保东老师、赵航老师等,基本上都退休了;连当年最年轻的张虹老师也退休了。其实呢,他们只是从形式上退了下来,大多仍然退而不休,在家著书立说——中国知识分子,哪有“退休”这一说呢。我一直还跟老师们保持着联系,读他们的文章,为他们的成就欣喜骄傲,还跟有的老师成为心心相印的谈思想、谈社会、谈时政、谈发展、谈学术、谈文学、谈人生、谈生活、谈孩子……几乎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老师们的睿智识见、深厚学问以及豁达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态度,至今仍然给我教益多多。
至于我们南开中文系,今天已经是南开大学文学院了,换上了一批又一批新的教学精英。除了汉语言文学系,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编辑学系,培养的学生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广受好评。如今在读的本科生也不是我们上学时的三四百而是逾千名了,还有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起点也比我们当年高得多。让我没想到的是,2004年,我的生命又一次跟母校系在一起,在当年我的研究生师兄、今天南开大学副校长陈洪先生和今天南开文学院党委书记乔以钢先生的主持下,我接过紫红色烫金聘书,成为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兼职教授。
当我第一次站在讲堂上,给今天的南开学子们讲课时,我就像30年前考入南开一样,激动得浑身颤栗,难以自持。母校啊,是您培养了我,没有当年您的谆谆教诲和严格要求,就没有我的今天!老师们啊,您们永远是我的先生,我一辈子都会以你们为楷模,不断走出人生的高境界,让南开精神薪尽火传,让你们安心,放心,开心!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