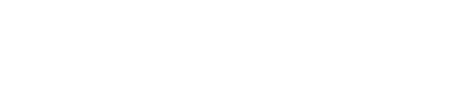黄桂元(中文系1977级校友,文学评论家)
我估计,这个世界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南开中文系,曾经有个叫做“诗魂社”的文学社团。它确实存在过,尽管即使在野史中也如同昙花一现。不过我们几位七七级的当事人,有时见了面还会以戏谑的口吻提到它。
“诗魂社”的确填充过南开大学中文系一段短暂历史。此前的大气候,是10年“文革”的寒夜沉沉万马齐喑。七七级学生入校之时正是1978年2月,一个早春的季节,政治气候的解冻也初露端倪。年龄参差,经历迥异,来自天南地北的同窗一脸沧桑地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自是激动莫名百感交集,既然是大学生,就没有不轻狂的道理,而中文系学生的轻狂则更是透着那么一股自视甚高的浪漫,尽管未来的一切还很模糊,但不整它个诗社、文学社什么的,就似乎白白上了一回中文系。孰料,系里一些冷静而高傲的老先生却兜头泼了一瓢冷水,称中文系从来就不负责培养作家,想当作家进中文系那算是入错了门。一下子便有了几天的沉闷,但还是有几个家伙不以为然,依旧踌躇满志走笔如飞,总觉得当代文学百废待兴,自己不出来拯救一番就简直是对不起后人。
由于我曾供职于天津某文学期刊,也发表过几首被归类于诗的东西,自然就有了些发言的资本。便常常有一些同窗拿着墨迹未干的诗稿找我,我也就似懂非懂地品头论足一番,反正法律上也没有误人子弟如何判罪的条款。其实,我的诗歌养分皆来自1976年前后的中国报刊。所谓的诗歌创作不过是些应景的政治打油诗和民间顺口溜,“诗坛”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军旅诗人李瑛和政治抒情诗人贺敬之,1950年代享誉一时的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和闻捷的《吐鲁番情歌》也只是在1976年底才接触。记得入学前我曾读了右派诗人公刘的诗集《在北方》,那种震惊使我蓦然醒悟,诗坛竟曾有过如此美丽的珍珠!凭着这点底子,我在七七级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成了诗歌“鉴赏权威”,如今想来已经笑不出来了,我们那一代人一度到了怎样贫乏的地步。我非常羡慕系里的那些小师弟小师妹们,他们的诗歌启蒙一上来就是超一流的,就是普希金、拜伦、惠特曼、叶赛宁、聂鲁达,就是里尔克、金斯堡、艾略特、庞德、叶芝、阿赫玛托娃,而北岛、舒婷们早已成了他们眼中的“古董”。文学启蒙上的落差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大致决定了起跑后的距离。不过,就像郭小川在一首诗里所说,年轻人,“我羡慕你们,却不嫉妒”。
记得入校不久,我们就接到了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徐敬亚、王小妮一伙人寄往全国各高校中文系的油印诗刊,王力、安志军、韩异、李辉和在下几个人看了认为还不错,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于是我们聚在一起商量着也搞一个诗社。在为诗社取名时,大家正值年轻气盛的青春期发育阶段,议来议去总觉得还应该更狂气些,后来我提出了“诗魂社”,算是通过了。我不清楚这是不是“文革”以后南开大学的第一个诗社。尽管诗社的几个人,如今早已是各辟蹊径面目皆非不知诗歌为何物了,我还是愿意把他们记下来,也算是听一下我们的青春绝响罢。一段时间,教室的墙壁上,开始不定期地出现“诗魂社”的作品。我们几个开始争相在稿纸上挤出青春期的情感分泌物。很快,实力派人物杨石主动加盟,才女李雅娟、朱维莉、白)林也款款而来要求入册,一时间“诗魂社”实力大增令人刮目,居然在系内外有些名堂了。
于是,我们经常在众目睽睽之下高视阔步,谈论着高雅的诗歌话题。在刚刚结束了文学封闭的年月,那种高谈阔论的感觉真是妙极了。
王力、韩异、安志军来自天津市,杨石来自武清县杨村镇,他们4人同龄,成立诗社那年都只有21岁。只是这4位除了喜欢写诗,在性情上南辕北辙。
此王力自然不是许多与之重名的彼王力们。王力平时显得沉静腼腆,但当他读了一部自认为“天才”作品后,会激动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如同有些人一旦喝多了酒就口无遮拦一样。一次他躺在床上读了《悲惨世界》,就在宿舍里不能自持地转悠起来,蓦地他扬起脸站定,面露红彤彤的神色开始无限崇拜地赞美雨果,这时他一定要称“雨果”为“维克多•雨果”,并必欲把另一类同样著名的作家不容置疑地贬为垃圾才罢休,与他后来谦谦君子的南开中文系教师形象判若两人。不过,能让心高气傲的王力看上眼的作家也确实不多。他最著名的为同学记忆深刻的口头禅是:“××作家,没才气!××作家,不懂艺术!”
韩异喜好神聊在那时就初露端倪,日后成了京城侃爷并不使人意外。我们住在一个宿舍,我对韩异的第一印象是,这完全是一介书生。那时学校里戴眼镜的不多,韩异戴的那副很秀气的眼镜欺骗了我。很快我就发现,在他那仿佛混迹过三教九流的社会经验面前,真正的书生是我。韩异思维敏捷,口才过人,常常把一件别人看来很寻常的事情抡圆了侃,且滔滔不绝全无倦色。韩异写起诗来却很安静,像一只猫,不声不响地闷头构思。或许得益于他曾读过两年技校,韩异写出的诗与他写出的字一样,显得比一般人更加严谨和规范。我记得他写过这样两首诗,题目老实得与韩异的本性判若两人:一首叫《水库》,一首叫《建筑》,听起来很像是一般的名词解释。韩异在公安系统干了多年,现在下海如鱼得水。他的聪明和潜能决定了他不会止于一种固定不变的职业,不知他是不是还保留着对诗歌的一段记忆。
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安志军,大约是同学中至今不改天津口音的一位。他少年老成,政治上不像有什么进取心,却喜欢读一些哲学书籍,与同学辩论起来一板一眼既沉稳又固执,很有一套歪理。他的脸清瘦而白皙,多年后与一位女同窗聊起当年往事,提起安志军,她说:“安志军?那个脸总是干干净净,像是刚刚洗过的男生?”他的诗个性突出,用词独特,几句读下来就可以知道此乃出自安志军的手笔。记得一次写作课上,当代文学的老师点评文章,她举出安志军的文章为例挑出修辞毛病,问什么是“闪窜”呢?课堂里立时发出一阵哄笑。从此,“闪窜”成了安志军的绰号。但就是这个“闪窜”,却“混”到了使人刮目的副局长位子,许多同学和老师为之大跌眼镜。也有人认为此乃必然,安志军的少年沉稳,七七级数一数又有几人?
李辉的年龄稍大一些,却性格内向。或许由于有些脱发的缘故,他永远戴一顶绿色军帽,很少在公众场合说话,更别提抛头露面。然而有一次班里举行诗歌朗诵会,李辉破例参加了。当他的声音回荡在现场时,所有的女生都睁大了眼睛,所有的男生都自卑了。不夸张地说,他的噪音条件和朗诵效果完全是专业水准。很快就有人推荐他去了学校广播站。李辉笔下的诗通常很短,却构思奇特语言怪异,经常有一些魔幻象征的意味。他曾有过一次痛苦的单恋,为了眼不见心不乱,一度他经常缺课,成了一个走读生,下了课就逃一般地躲回家里。我想象他那时的爱是深刻而沉重的,也是美丽而寂寞的。
从“斜刺里”杀到“诗魂社”的杨石,平常的谈吐于高傲之中透着随意而幽默。然而有时在公众场合说话,又正儿八经面容严肃地像是换了一个人。他的诗歌既有莽莽苍苍的奔放,也有婉约细腻的柔情,词采丰赡华丽,属于才子型诗风。杨石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常常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随口说出一些与之相关对应的文学描写和诗词警句,令人忍俊不禁。虽不无炫耀之嫌,但炫耀本身也是需要资本的。1990年后,他东渡扶桑留学,不久把家小也搬到日本。几年前,他又把家小统统接回天津,为的是让孩子浸泡在中国文化的氛围,自己则风尘仆仆地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投资做生意。他在商场表现出来的老到和精明同样令人不敢小视。不久前,中文系部分同学合股注册了“天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杨石被推举为董事长,就不是偶然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了他的一个电话,他说,刚刚读了我最近出版的系列随笔集《驿路芳踪》,便有了与我通话的冲动,语气里充满了真诚的感慨。日后他还同许多人提到这部书,有如此真诚的读者我自然高兴,何况还是一位“诗魂社”的同道和如今的“日商”。我对他遂有了更深的认识,也由此相信,杨石永远不会成为那种只懂得生意的商人。
新加盟的三位女生,李雅娟现在是天津司法局的一位律师,朱维莉执教于北京公安政法系统的一所大学,白)林则同也是我们班同学的朱毓朝移居加拿大多年。淳朴的李雅娟来自武清县,与同乡杨石同岁,写诗也用“村姑”的笔名。她的诗受古典诗词影响很深,不拘一格却率性质朴,一如她的本色为人,这种特征一般是不大容易改变的。她日后成了一个律师也是我所料想不到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律师一般做事严谨、认真,说话极富于狡辩,这都与我印象中的李雅娟的散淡性情不大相符。
远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白)林,曾很长时间担任七七级的团支部书记。她长得瘦小玲珑,却生性大方开朗,善解人意,乐于助人,诗写得也很有才华。上学时她已经24岁,是最先在班里与本班同学谈恋爱的女生,丝毫没有顾忌什么,落落大方我行我素,而且始终没有因为有了男朋友而影响了自己在男生中的威信,我觉得这也是做女人的一种才华。许多年了,我们同学一直没有忘记他们这对夫妇。
相比之下,朱维莉是一个平时不爱说话,说起话来细声细语的腼腆女生,脸上常常露出羞涩的微笑,像只可爱的小兔子。她来自新疆北部遥远而寒冷的阿尔泰地区,父亲是那里的专员,除了经济上要远远好于一般同学外,本人在大家看来是一个长相很乖毫无骄娇二气的女孩。她显得岁数挺小,其实比王力、韩异、安志军、杨石、李雅娟都大一岁。她喜欢运动,动作富于美的节奏和弹性,像是一只奔跑的小鹿,只是一写起诗不得了,那句子里的形象、意境大气得使一般须眉自惭不如。我总觉得朱维莉的诗歌想象力得益于新疆的辽阔地域。她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乌鲁木齐教书,沉寂了一小段时间,就一反平日被动的性格,借在北京进修学习的机会,主动向同班一个很出色的男生发出了爱的试探信号,对方心有灵犀,俩人最终定情于京城,神奇、浪漫地成为了我们班的第六对夫妻。
“诗魂社”未到第四学年就寿终正寝,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因为此时,七七级的“南开文学社”已经有了更大的影响,“南开文学社”自然属于五脏俱全的庞然大物,而里面的诗歌组其实就脱胎于“诗魂社”。只是一段时间我们这些当事人总也改不了口,还总爱说“咱们的‘诗魂社’”如何如何。后来渐渐地就真成野史了。